“人参当零食”曾酿成大病
话说康熙五十一年(1712)七月初,江宁织造曹寅即曹雪芹祖父感受风寒,卧病数日,日渐虚弱。医生说得的是疟疾,但经多方诊治无效,曹寅遂向康熙皇帝求救。康熙闻后立即命人星夜快马送药,并详细嘱咐了此药的用法、用量和禁忌等,其中提到“曹寅元肯吃人参,今得此病,亦是人参中来的。”康熙爷认为曹氏此病是因常吃人参郁热内积而感。常言道,“人没内火,不感外寒。”疟疾是经按蚊叮咬感染疟原虫所引起的虫媒传染病,曹寅是否真得了疟疾现已无从考证,但外感病用补药确是中医大忌。而爱吃人参的曹氏没等到“主子圣药”就于七月二十三日病逝了。
无独有偶,明代医家缪希雍,年轻时就好服补药,甚至把以人参为主组方的丸药当“零食”吃,后来也酿成大病。据其好友、同为江南名医的王肯堂回忆,明万历七年(1579),两人初识时他就见缪氏常从袖口里掏出丸药嚼食并得知此方名资生丸。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王肯堂在《证治准绳·伤寒》里记载了他为缪氏诊病案例:缪氏发热不退,其他医生投寒凉疏解之方均无效,王肯堂深知其生活嗜好,判断此病由常年大量服用滋补药所致,遂遣方开药,终使良友转危为安。可见人参等滋补药不能长期、随便当“零食”吃。
人参自古“药草”而非食材
人参属植物,自古就用来治病而非养生。人参的“参”字原作“蓡”读为“jìn”,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里就说:“蓡,人蓡,药草,出上党。”中国最早的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将人参归到上品,说它既可“除邪气”,也有扶正功效,如“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止惊悸”以及“明目、开心益智”等。
但是,当笔者检索现存29部传统食疗学专著/篇,从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食治》(652年)到费伯雄的《食鉴本草》(1883年)都没有收录人参,即自唐至清,人参都仅是“药草”而非食材。
“药膳”是缺乏医学专门知识的误读
不仅如此,所谓“药膳”,也并非出自医书而是史籍。笔者借助《中华医典》光盘,检索秦汉至新中国成立前现存1156部医书,均未见“药膳”提法。“药膳”之名最早见于《后汉书·列女传》,但《后汉书·章帝八王传》里也有“膳药”之说,史籍中还有“方药羞膳”“尝药视膳”和“膳药羞饵”等说法。施受药膳者均发生在慈祥父母与孝顺子女以及宦官、后妃与帝王之间显示孝行和起居照料时。制作药膳者虽语焉不详,但绝非“司药”“司膳”和“御医”等专业人士所为。《二十五史》和《十三经》中提及“药膳”的20处记载均无具体药膳名称与配方。再从古汉语书写无标点、单音节词偏多特点分析,史籍中的“药膳”当为“药”和“膳”的并称。将非医古籍中的“药膳”解释成复合词,是缺乏医学专门知识的误读。
“以药入食”多用于病证调理而非养生
古代确有以药入食情况,如张仲景治“寒疝腹痛”的当归生姜羊肉汤和治“心中烦、不得卧”的黄连阿胶汤,但按原方比例,不加任何调味品煎煮成的汤药味十足,全无羊肉汤、蛋花汤的口感和品相。将药物添加到食材中做成粥食等膳食形式,古代亦很常见,如世界上最早的老年医学专著、宋元时期成书的《寿亲养老新书》中“人参粥”就为“治反胃吐酸水”,清代医家章穆在《调疾饮食辩》中也挑明了说人参粥只能是脾肺气虚者才能喝。“以药入食”多用于老人、小儿、孕妇病证调理,首先为治病,其次顾护胃气,用于养生者,多有民俗和宗教背景考量,前者如春节饮屠苏酒、端午节饮雄黄酒以防疫辟秽,后者如道教文化中的服(石)食以冀成仙。
根据国家卫计委“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物质目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国卫办食品函〔2014〕975号文件规定,现代将人参当作保健食品原料,在用法用量和不适宜人群方面有严格限制。即必须为5年及5年以下的人工种植参,食用量应该≤3克/天且孕妇、哺乳期妇女及14周岁以下儿童不宜食用。(林殷 范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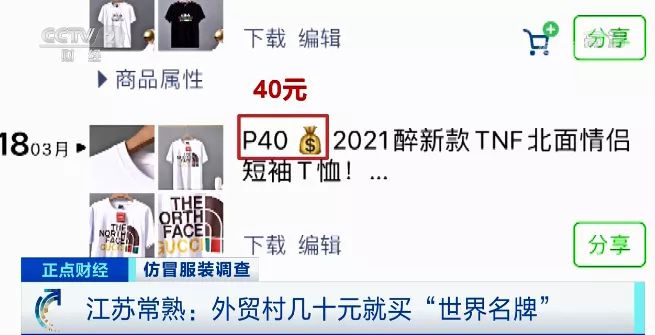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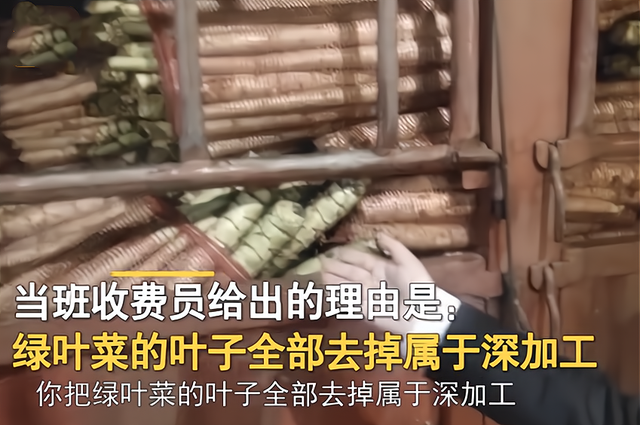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40741号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40741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