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钱是谁还的、什么时候还清”的问题,胡小凤也用了“当然”二字,“我爸还的,那时候我还在上学,也得花钱。幸亏是向我二姑借的钱,我爸说慢慢还吧。那时候,我爸年纪已经很大了,但还在工地做小工,天天累得不行。钱是什么时候还清的,我也忘了,反正也有一两年吧”。
在北京做小时工的杨英则更加辛苦,一夜返贫——为了支付结婚费用,家里倾其所有,还欠了15万元的外债。
即便不容易,但在记者走访中,几乎所有受访的父母都把为子女置办婚事当作自己的责任与义务。如果子女未能如期订媒结婚,父母则会自认为是他们的“问题”,是父辈的“不称职”或“不误正业”造成了子女的婚姻困境。
“不仅我们自己这么觉得,周围人也这么觉得,这让我们的心理负担太大了。”陆大力说,他已经不能干重活,家里经过这几年的消耗,积蓄已所剩无几,“要凑齐10万元左右的彩礼,至少还要再借7万元,但一年的收入只能勉强还上年息”。
对于彩礼,陆元盛还想过一个办法——分期付款。不过,这个办法很快被女方家长顶了回来——“你以为买房呢”。
现在,陆元盛决定过完春节就换个工作,以期更高的薪金,因为“没钱就更没机会了”。
“天价彩礼”怎么算
“天价彩礼”是怎么算出来的?
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记者得到的回答可谓是“惊人”。
在调查过程中,记者不止一次听被访者说——“我们这里就是‘卖’女儿啊”。
地域是一些家庭评判彩礼钱的一个标准,很多家长会要求女儿不要找外省的对象。这其中有文化冲突的考虑,但更重要的是养老问题,跨地域所牵扯的养老问题往往会使彩礼价格上升。
在北京工作的李女士告诉记者:“我妈妈不希望我找外省的,10万元彩礼钱是底线,没有商量的余地。将来订婚,只增不减。如果男方是外省的话,彩礼钱至少要20万元。妈妈认为,如果我嫁到外省,回家不方便,无法照顾和赡养老人。”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的研究人员曾对彩礼形成因素进行专门研究,他们发现,虽然社会变革使得人们的认知观念发生了改变,但是观念的最终落脚点仍是价格的商定。社会变迁虽然使得个体的流动性增强,依靠个人的人力资本获益的可能性增大。但正是因为这样,由于社会变革所带来的种种不确定性,使得家庭更加注重通过提高彩礼来降低未来的风险。
在北京白领王宁宁的记忆中,讨论彩礼就像一场拉锯战,而这样一场拉锯战或许正是一个缩影:
2015年2月,女方家长会见家族长辈,商讨彩礼事宜并准备起草“红单”(红纸上标明彩礼价钱与相应的实物等,实质上就是一张婚嫁凭证。同时,“红单”必须由长辈起草并双方签字方为有效)。女方家长提出的13.9万元遭到家族长辈的强烈反对:“你供她读书就不止10万元,13.9万元你能得到什么”“村姑都不止十五六万了”“人家二婚的都18万啊”“这么低的价格,你也别谈彩礼了,就让他们夫妻负责养老吧”。
最终,家族长辈参照婚姻市场中的标准价格并根据待嫁女王宁宁的学历资本,提出了20万元的彩礼定价。
不过,女方家长为了减轻女儿将来的经济负担,还是抵住压力,坚持13.9万元彩礼价格,不过将回嫁妆部分改为3万元,即女方家长净得10.9万元。此时,家族网络再一次发挥了它的作用,彩礼的商定变为对传统程序的遵循。
家族长辈说:“按规矩,‘红单’签下去,彩礼的钱就必须一次性付清。”于是,在“红单”起草完,长辈尚未签字之前,女方家长给男方家长打电话确认,是否能一次性付清13.9万元。
男方家长在得知“红单”签下就要付清彩礼钱款的规矩后,由于经济上不能一次性付清,便提出不签“红单”。家族长辈因此很生气,不允许再谈订婚事宜,订婚宣告失败。
“在我家里人看来,13.9万元并不高,农村女孩的彩礼钱都十五六万元了,一个准研究生还只要13.9万元,这已经是我们家的底线了。其次,男方提出订婚,结果最后却是男方提出不签‘红单’,决定权不在我们,反在男方,这让我的父母觉得很丢人。”王宁宁说。
本报记者 赵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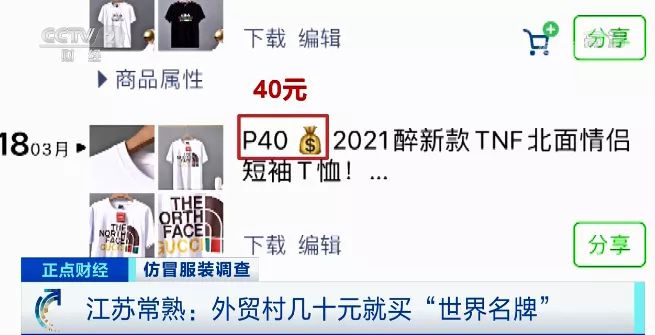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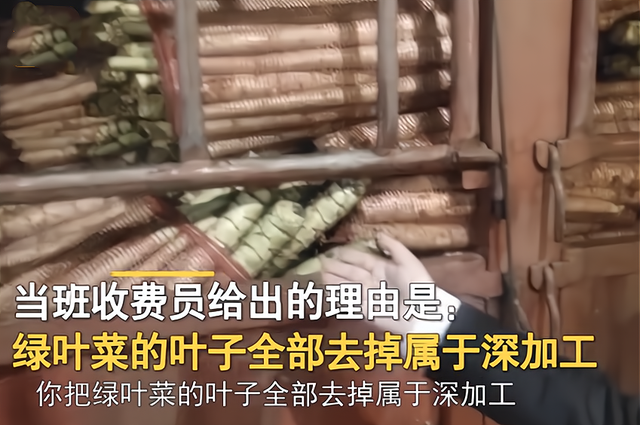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40741号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40741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