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南海大计划”
对南海深部的认识应以中国人为主
新京报:这个航次算是“南海深部计划”的收官之作,对您来说有什么意义?
汪品先:这应该是我这辈子做的最后一件比较大的事情。2011年“南海深部计划”立项,我当时就说,点一把火炬,它会烧起来的。
新京报:为什么这么说?
汪品先:因为南海对中国太重要了,各个部门都愿意参与进来。“南海大计划”从2011年到现在,立了60个项目,其中51个都是重点项目,一共32个单位、700多人次参与,规模很大。
新京报:也就是说, “南海大计划”包含了各种综合科学?
汪品先:对,我们立项的时候叫做“南海深部过程演变”。“深部过程”是什么意思?就不是现在在采石油的那些地方,而是到南海中间一个菱形的4000多米的区域,底下是玄武岩。它形成了才有南海,我们就攻这个部分。
新京报:具体来讲,包括哪些研究学科?
汪品先:三个方面,一个是构造,南海的构造和南海的岩浆作用,可以比作是“骨头”;第二个部分是沉积和古海洋学,从南海的沉积物里恢复当时的海洋演变,我把它比作“肉”;第三个是生物地球化学过程,我把它比作“血”。
这三样东西做成一个麻雀,我就来研究这个麻雀的前生今世怎么运行。
新京报:“南海大计划”取得了哪些显著成绩?
汪品先:大计划中包括3个大洋钻探、3个深潜航次。我敢讲,这是中国海洋基础科学研究中到现在为止最大规模的。
我们明年春天计划开总结会,2019年“交账”出来是很漂亮的,它会改变我们对南海以往的看法,大概会成为世界上边缘海最好的研究计划之一。
我们把今年这个航次比作是跑道上最后一圈,所以我说我自己一定要下来。
新京报:经过这么多年的探索研究,“南海深部计划”最后会呈现给公众什么结果?
汪品先:我们希望拿出一个边缘海的产生演化和运行的典范来。世界75%的边缘海都在西太平洋,但我们了解很不够。
我们现在把南海作为一个切入点,最后我想向世界表明,南海深部的认识是中国人为主。之前都是外国人在做工作,但跟我们现在的规模不好比。
我们会有很多很漂亮的结果,信心很足。
新京报:“南海大计划”后续还有哪些工作要做?
汪品先:除了科学方面的工作,我们还准备做一些科普工作。
南海的科研成果完全可以介绍给老百姓。我们花了那么多钱,到底做出什么来了?这个是可以说清楚的。
谈科研一线
科学家只有在前线才会发现问题
新京报:现在很多年轻人也在做这个工作,为什么你自己还要亲自下潜?
汪品先:我们现在在建设硬件方面十分下功夫,但在软件上出现了问题。很多人当了学科带头人以后就不干第一线了,让学生去干。比如现在很多到海去采样的工作,都是打发学生去采的,科学家就坐在办公室里。
这跟国际上惯例是相反的。外国科学家也会有学生帮他做,但第一步的采样一定是自己带头做。
我这些年没有少批评人家,我觉得说了也没用,自己做一下是最好的。对于培养年轻人,我想用行动影响一些人。
新京报:亲自下潜,是不是您的研究经验也起到作用?
汪品先:对,我们本来计划要去看珊瑚礁的,结果去了以后,发现冷水珊瑚林,就改变了计划。
第一次发现之后,我让年轻人接着去过,但没有完成任务,我自己就得再下去。你自己不去,没有人替你做。包括我把这个课题提到此次航次的重大位置,只有科学家自己在船上,才敢这样。
新京报:所以这次下潜是想通过自己的行为来影响别人?
汪品先:不是全为了这个才去做。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我这个年龄是错了位的,该做事情的时候做不成,该退的时候反而可以做。
所以我现在在国际上很滑稽,跟我这样年龄的学者一般不出来。但我现在还在做,因为我丢了好多年。
我最好的年龄在搞革命,后来又没有条件和资金,只能跟外国人合作。现在有了条件,自己当然要做。说了那么多年深海,趁我现在还走得动,一定要去看看。
新京报:海洋科学发展方面,您还有什么担忧的问题?
汪品先:中国可能是世界上科技投入增长最快的国家。去年,我在国际会议上提出来,中国要做什么什么,国际上的反应很不一样,有的支持,有的不吭声。
我就希望中国的科研队伍真能够在国际上站住,这不光是科学问题,包括政治、外交问题等等。怎么做好这些事,这个才是难题。你说你自己去潜一次海,那又能怎么样?
新京报:您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海洋研究,几次南海科考是不是也见证了中国海洋科学的发展?
汪品先:确实反映了中国海洋科学在变化。上世纪70年代末,海南岛西边的莺歌海打南海第一口探井时,我在岸边为石油井做鉴定。1994年,我参与南海第一个古海洋学专题航次。1999年,担任首次南海大洋钻探的首席科学家。2005年,担任同济大学与法国合作举行的“马可·波罗”航海科考首席科学家。
那几次依靠的都是外国装备。而这一次,是我们自己造的装备,国产化率达到95%以上。
我的这些经历反映了中国海洋科学从弱到强,从封闭到开放,走向国际前沿的一个过程。而这次中国自己有手段能够去做国际水平的工作,所以就特别高兴。
新京报:您说过“海洋事业迎来了郑和下西洋600年以来的最好时机”,为什么这么说?
汪品先:我说这话其实是与中国的大陆文明和海洋文明有关。
我觉得东西方差异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东方文明是大陆文明,西方文明是海洋文明。直到15世纪分不出谁好谁坏,大家各自发展。16世纪之后,特别是中国到了18世纪以后,我们一下子醒过来。
大陆文明有很多好的方面,但是对于创造性的发展和个性解放是不利的。
我认为海洋文明有利于创新,现在我们从国家领导人到老百姓,海洋意识都更强了。
谈未来安排
要做的事按重要性排序,也许哪天就“跑掉了”
新京报:您身体状态这么好,平时锻炼身体吗?
汪品先:年轻时会长跑、游游泳,自行车骑得很多。有时候想到一个科学问题,我来劲了,在街上骑两个钟头。
新京报:现在还会骑车?
汪品先:我之前骑车上班,现在老伴不让我多骑车,叫我多走路,走路也重要。
我的生活方式比较简单,看不出休息和工作的差异。科学家如果对工作提不起兴趣,还是别干。你自己要有精神,在船上谁不吐啊,但讨论起问题来劲的话,这些都是小事情。这是我的优点,到现在我还是很投入的。
新京报:您现在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
汪品先:我现在是倒计时的,后面我要做的事情都按照重要性排着队。
先把我的“南海大计划”完成,如果还有几年,再做别的重要的事。今年还有两本中文的书,本来也不准备出,后来一个老朋友去世,我想搞不好我也跑掉了,所以就出了。
怎么说呢,要叫我做的事我不想做,我就不客气了,是不会做的。
新京报:所以时间对您来讲,是很宝贵的。
汪品先:我觉得自己能拿得出手的文章,都是60岁以后完成的。所以我开玩笑讲,人家是博士后,我是院士后。
像地球科学、宏观生物学,眼界和经历很重要,你没见过这个东西,怎么会理解?积累多了以后,自然会有很多联想,这恰恰就是年纪大的人的长处。
新京报:以后会把重心放在哪里?
汪品先:我自己还想做一些人文方面的事。我这次随船带的是一个日本华人写的中国史,来北京带了林语堂的《苏东坡传》,这都是为后面写东西做准备。
我总觉得我们这代人的经历很宝贵,想把它记录下来。明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我也想写点东西,有些问题需要继续思考。
新京报:未来还会再进行深海下潜吗?
汪品先:不知道。船长给我讲,等到他们1万米的(深潜器)造好后,让我再去,我说我不知道那时候人在哪里。
我更喜欢让我后面的时间自由一点,我在推中国深海研究进入世界前沿,我自己在做,也希望一些年轻人能够去做。
记者 王俊 倪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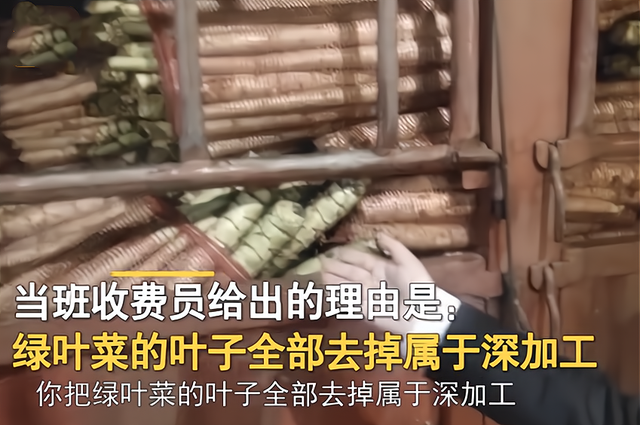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40741号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40741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