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中国科学界积极培养“新鲜血液”。1955年,张弥曼被送到莫斯科大学学习古生物学。但是,这位地质学专业的学生,完全不知道该学哪类古生物。
“学鱼!”当时在苏联访问的鱼类学家伍献文先生建议张弥曼。
张弥曼自称“是一个立了理想,怎么也不会改变的人”。她听了伍先生的建议,从此开始了对鱼化石的研究。张弥曼经常到莫斯科河岸边的全新世沉积中采集鱼化石,夜里用小船撒下横跨莫斯科河的鱼网,清晨把撞在网上的各种鱼类采集下来,用来和化石进行对比,以探究古鱼类同现代鱼类之间的关系。
1960年,张弥曼回国,进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工作,开始了她的寻“鱼”生涯。年轻时每年约有三个月,她都随地质勘探队在荒野采集化石。“野外勘探是基本功,再远我也能走下来,而且不比任何人慢。”
那时,野外勘探基本靠腿,一天步行20公里,是家常便饭,很多时候只能投宿老乡家,或在村里祠堂的戏台上过夜。由于消耗太大,地质队员们都如“饿鬼”一般。有一次,恰逢中秋节,队里发了一斤米饭,一斤烙饼,张弥曼竟就着酱豆腐一扫而空,创下“个人纪录”。
“每次身上都带着虱子,回家进门前要先把衣服煮一遍。”回想起这些,张弥曼眼中绽放快乐的光彩,“那时候,衣服没有化纤,确实经煮。换成现在,放进开水锅恐怕就捞不出整件的衣服来了。”
“我是一个幸运的人,总是能遇到好老师。”她说,“伍老当年的一句话定了我的‘终身’,但谁说媒妁之言的婚姻就一定会不幸福呢?”
为纪念伍献文先生,2008年,张弥曼将在柴达木盆地发现的一种奇特鱼化石命名为“伍氏献文鱼”。

“不睡觉”的中国女人
“越来越多的鱼化石显示,鱼类登陆这一关键环节就发生在中国云南。而张弥曼是这一大发现的开拓者”
约4.3亿年前到4亿年前,云南东部还是一片处于赤道附近的热带浅海。海里陆续“游”出了包括晨晓弥曼鱼、斑鳞鱼、杨氏鱼、奇异鱼、全颌鱼、麒麟鱼在内的“明星物种”,谱写了鱼类从海洋向陆地演化的关键篇章。
“晨晓弥曼鱼”的命名者、古鱼类专家朱敏说:“它是献给我的老师、中国肉鳍鱼类研究的开拓者张弥曼女士最好的礼物。”
在生命“进化树”上,人类属于四足动物。大约在3.8亿年前,肉鳍鱼类登上陆地,演化出了四足动物。但哪一种肉鳍鱼类,才是人和鱼的最近共同祖先呢?数百年间,这个“谜”在古生物学界悬而未决。
1980年张弥曼访学瑞典自然历史博物馆,看到瑞典学派代表人物雅尔维克用25年时间还原的肉鳍鱼化石。震撼之余,她决心用最短时间“追赶”上去。那时,没有CT扫描技术,想从内到外“看清”微小的鱼化石,需要一种极为复杂的连续磨片及腊制模型方法。
张弥曼还原的是云南曲靖的杨氏鱼。它的颅骨化石只有2.8厘米长,张弥曼需要先磨掉极微小的一块,在显微镜下画出切面图,直到整块化石完全磨完为止。
她画了540多张图,把它们贴在平整的石头上,用熔化的石蜡和蜂蜡,制作出薄薄的拓片,再将剖面图雕刻出来……最后,所有的剖面“拼装”出一个20倍等比例放大的标本。
渐渐地,博物馆里的人都知道这个中国女人“不睡觉”。于是,有人给她搬来躺椅;有人在她桌上放一束鲜花,以表达敬意。就这样,她仅用两年完成了这项研究。
按照瑞典学派的观点,杨氏鱼应有一对内鼻孔,头颅分成前后两半,由一个颅中关节连接。张弥曼在做这个鱼标本时,既没找到内鼻孔,也没找到颅中关节。内鼻孔是鱼类“登陆”时学会呼吸的关键构造。由于她的工作无可挑剔,人们开始对内鼻孔的起源,乃至四足动物的起源有了各种新的认识。
后来,她用更多证据动摇了瑞典学派的权威,认为杨氏鱼和奇异鱼都是一种原始的肺鱼,在国际古生物界激起轩然大波。但张弥曼说:“真理不辩不明,从不后悔这么做。”
直到1995年,世界古生物学界才普遍认同她的观点,肉鳍鱼类起源的中心地区也逐渐从欧洲和北美转向了中国云南曲靖。
“越来越多的鱼化石显示,鱼类登陆这一关键环节就发生在中国云南。”朱敏说。“而张先生是这一大发现的开拓者。”
40多年过去,张弥曼那双巧手因为总拿着小钢钎在化石上敲敲打打,指纹都几乎磨平了。

抽掉“踏脚板”
“我小时候所受到的教育就是平等和诚实。把错的、对的都摆出来,对科学有益处。我很喜欢人家不同意我,也喜欢看年轻人比我们做得好”
在1942年拍摄的一张与小学老师和同学的合影中,大家都正色看着镜头,唯有张弥曼歪着头,探出脚,毫无旧时女子该有的“端正”。她说:“我从来没有尊卑观念,因此也惹了不少麻烦。”
在“十年动乱”期间,张弥曼被送到农村改造,她坦然面对,退掉城里的房子,做好了一辈子回不来的准备。“我本来就是从农民中来的,回到农村又怎样呢?”
张弥曼的丈夫是她莫斯科大学的同学,学物理,回国后去了戈壁滩,搞原子弹和氢弹研究。女儿出生一个月,张弥曼就送她去了上海外婆家。从此,一家三口分隔三地多年。女儿十岁时,她才将其接回自己身边。
“我们这一代人,自己的事情都是可以牺牲的。”她感慨地说,不管是科学研究,还是工作都抱着一颗“公心”。在她看来,古生物学的“公心”就是“不到死也要抱着化石不撒手”。
她最敬佩的学者是已故的英国古生物学家柯林·帕特森。她记得柯林在一篇论文中,曾大胆提出一种观点,并写道:“我们这样做,几乎是把自己脚下的踏脚板抽掉。”化石材料,就是每一个古生物学家的“踏脚板”,吸引着科学家进入未知而引人入胜的世界。
张弥曼在科研中是有勇气抽掉自己“踏脚板”的人。上世纪90年代初,她把炙手可热的“金矿”——泥盆纪鱼类研究,移交给了朱敏等年轻人,转而研究很多人不屑的新生代鲤科鱼类化石。彼时,六七十岁的她,去过青海、新疆野外勘探。她说:“年轻人做得比我好。”
朱敏说,当了老师的张弥曼从不责骂学生,但“她淡淡地说几句,你也受不了的”。因为,她的严谨是学术圈出了名的,也不会绕圈子,说出的问题往往切中要害。
“我小时候所受到的教育就是平等和诚实。”张弥曼笑着说,把错的、对的都摆出来,对科学有益处。“我很喜欢人家不同意我,也喜欢看年轻人比我们做得好”。
鲤科鱼类化石分布广、比较常见,很难在短时间内发表高质量的论文。她说:“我不是没有思想斗争。但是没有寂寞、枯燥的基础工作,怎么会有真正的大发现?!”
鱼类分布严格受水系格局的限制,因此,新生代鱼化石研究可以揭示诸如古气候、古水系格局、古高度等古环境因素,进而协助重建地球变化的历史。
近年来,张弥曼和她的同事在青藏高原上发现了丰富、保存精良的新生代鱼化石,将有助于揭开这一地区“演化进行时”的历史。比如,伍氏献文鱼,其全身极度增粗的骨骼,可能是随着水中钙盐浓度升高而逐渐变化的,“今天我们说高原干旱化的故事,还有什么比它更生动呢?”
有人不明白:对古鱼类的研究跟今人生活有何关系呢?张弥曼说,没有直接关系。但这个研究能帮我们认识生物演化,而关于生物演化的科普能激发孩子们逻辑思维的萌芽,“这些对于地球和人类的未来很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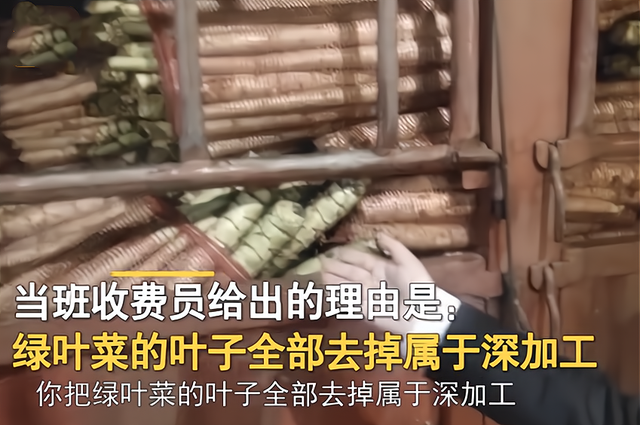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40741号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40741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