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央广网北京8月18日消息(记者冯会玲 刘柏煊)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赵忠贤,1941年出生,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高温超导研究奠基人之一。人类发现超导百余年来,高温超导研究总计有两次重大突破,他所在的团队都做出了重大贡献:独立发现液氮温区高温超导体,以及发现系列50K以上铁基高温超导体并创造55K纪录。2017年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同年获得影响世界华人大奖。中科院物理研究所所长王玉鹏这样形容赵忠贤的:“他爱憎分明,性格很鲜明的一个人,都知道他这种直率的性格。科学上就是越直率越好,用不着绕弯子,科学一就是一,二就是二。”
“我做研究真的从来没想过拿奖,我的个人想法,我们做科学研究实际是在为人类的文明添砖加瓦大了点,就加上一滴水吧,汇集到人类文明的长河之中。第二是满足国家的科技发展的需求。”1987年,美国物理学会年会在纽约举行,这个被称为“物理学界摇滚音乐节”的大会临时增加了“高临界温度超导体专门会议”,只能容纳1000人的大厅挤进了3000人侧耳聆听。报告从晚上19点30分开始,一直讲到凌晨3点15分。46岁的中国科学家赵忠贤是当晚51名报告人中,最耀眼的五个“特别报告人”之一。
那是那个年代中国人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少有的亮相,同时也标志着中国高温超导研究跻身国际行列。

当年的实验设备极其简陋
超导体在能源、医疗、信息、交通等领域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是21世纪战略性技术储备之一。从1911年人类发现超导到现在,百年间,各国科学家为了寻找超导材料,苦苦摸索。中国超导研究起步时,就已经整整落后了50年。赵忠贤和他的团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硬是追上了世界一流研究者的步伐。
赵忠贤介绍说,“当时干劲很足,但条件确实非常差,我们自己绕个炉子烧样品。临界温度高了以后,原来的测量系统就要进行改造,好多设备都是自己现做的。那时夜里不睡觉,困了就在椅子旁边靠靠,有事叫起来再继续干。”
如今已是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的闻海虎曾在上研究生时重复赵忠贤做过的实验,测一条曲线要不休不眠两天两夜才能完成。他感慨,赵忠贤他们一穷二白起步,设备修了坏,坏了修,实在无法想象该有多难。“盯着仪器上的表一个一个地记录,不像现在都是计算机采集,计算机一划就出来了。那时每变温一次,要调一下气压、气流,让它变温,等温度稳定了在表上读数把它记录下来。”

赵忠贤骑三轮车去买蜂窝煤
在美国的那场报告结束后,赵忠贤回到北京,脱下西装,换上夹克,蹬上三轮去买蜂窝煤,一时间,院士蹬板车传为美谈。赵忠贤知道后乐呵呵反问:院士就不烧蜂窝煤了?赵忠贤指着照片说,“正好我在美国买了一个照相机,儿子拿了以后说来试试看好用不好用,我一蹬板车,他一按就按下来,照片就出来了。我们那个年代的人这种事情认为都很正常的。”
院士家要烧蜂窝煤,要存大白菜,还要一边看书一边看孩子。与众不同的是,赵忠贤看娃有绝招,撒一把爆米花在干净的床单上,让儿子转着圈捡着吃,吃完了他再撒一把,赵忠贤笑称一举三得,孩子多爬,还有助提高智力。
对赵忠贤来说,生活的不易,实验设备的简陋,都不算什么,寻找液氮温区的高温超导体、甚至室温超导体才是日夜萦绕在心头的主题。他说,“超导体有几千种,应用的没有几个,因为好多材料还有其他性能,譬如超导性有了,通电流如何、加磁场如何、机械性能如何……都有其他问题,其中选择一个能用的材料很少,所以要不断地找,还要找更好的。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不断前进的主题。”

赵忠贤依然坚守在科研一线
百年探索,任何一点突破都举步维艰,失败似乎总是接踵而来。一拨又一拨的人心灰意冷地散去,或转了研究方向,或下海经商,因为赵忠贤的热爱,他没有挪动半步,铁了心要扎根超导研究。
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的赵忠贤念旧,他常常会想起寒冬腊月,课上到一半,讲台上的先生吆喝着大家一起跺脚取暖;也记得张宗燧先生,再冷的天,常能讲出一身汗,热得要脱掉蹭满粉笔灰的毛衣。他当然更不舍得忘记当年先生们的教导:安心为国家做贡献,哪怕苦守冷板凳。
赵忠贤介绍,“给我们上课的有严济慈,力学系上课的是钱学森,给这个数学系上课是华罗庚。他们上课的时候不管教学大纲,他想怎么讲就怎么讲。科大力学系的第一届学生到了暑期毕业,当时钱学森是系主任,说他们的基础还没打好,晚毕业半年,再补基础。我们当时没想太多,就是要好好学习,科学上能够老老实实干事情。”

赵忠贤获得2016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板凳坐得十年冷,凭借超导研究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年逾古稀的赵忠贤却没有半点停歇。他心里较的劲儿,就是超导研究突破的每一步,中国人绝不能再落下,要走在前面。“我们通过一番努力,也许没有得到重大的结果,但是我们做的东西,就是给后人,给下一代人,他们会在这个基础上会有所发展。”
【记者手记】
我是记者冯会玲,老家辽宁的赵忠贤有着东北人的幽默,别人问他,一辈子耗在超导一件事上,不枯燥吗?他答,我们每天也有新发现,就跟爱打麻将的人一样,分大和、小和,很有意思。别人开玩笑说他最初的那些设备实在土得掉渣,他一本正经解释,那些土大炮可都是有功之臣,绝口不提当年到底有多难。
可是心里哪能没有遗憾?他也忍不住感慨,当年要是有现在1%的条件,我一定比现在做得好。不管中国的超导研究被世界瞩目,还是经历低谷,他始终不离不弃,就是因为他坚信:大树只有扎根下去,才能枝繁叶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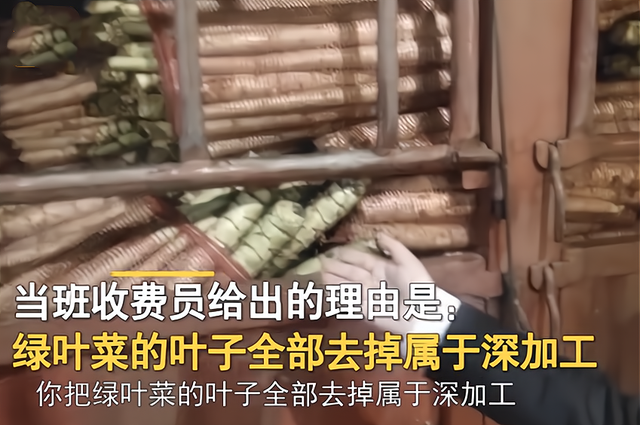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40741号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40741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