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辈子外交官,吴建民向全世界讲了无数次中国道理,也听了许多个国家的故事。2012年回访高中母校,他提笔写下六个字,“爱祖国,爱人类”。他要母校的孩子们记住,这两件事并不矛盾。
钓鱼岛撞船事件的次年,日本发生“3·11大地震”。日本人佐藤充救完20名中国的研修生,才返回险地营救妻女,最终被卷入水中遇难。吴建民在国际会议上遇到一群日本人,主动讲起这件事。会后,日本人纷纷向他鞠躬道谢,甚至感动落泪。可这件事在日本没有得到报道。在中国,也仅仅是一粒投入水的小石子,很快就无声无息了。
晚年的吴建民在书里表达疑惑,为什么国家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是有人一意孤行。有人高呼“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吴建民反驳:“利益最大化?听起来挺美!其他国家怎么想,利益最小化吗?这可不是合作共赢。”
欧美国家制造“中国威胁论”时,吴建民一板一眼地分析不理智情绪,“国家如同人,自身发展遇到问题,情绪就会敏感,对外界的反应就会过分。”可过了几年,他发现,一些同胞也有类似的倾向。
他忧心忡忡地记录:代表团来欧洲,不再像当年一样谦虚学习,而是指着巴黎说,“全都是老楼,有啥好的。”一些邻居成了部分人口中的“小破国”,和另一些国家则“不惜一战”。
法国人、英国人、印度人都不安地来问早已退休的他,“你们国家是不是真的想打仗?”
吴建民心急。驻外生涯结束时,要写最后的总结报告,他列了一堆外事活动中还有的问题,写了篇“启示”。
吴建民转回头,用和当年一样的劲头儿,把曾经说给外国人听的“和平友好”再强调给国内的同胞。
亲朋心疼他岁数大,说“档次不高的活动就别去了”。同事好心提醒,“咱就别出去讲了,容易挨骂。”可他说,“就是要听老百姓的声音”,他们才是国家最生动有力的形象。
吴建民回忆上世纪90年代,丹麦的外交官说,“中国人真好。”他还在读书的儿子来中国体验生活,爬上绿皮硬座车厢,把臭袜子一塞就睡着了。醒来后却发现笑眯眯的老奶奶把袜子帮他洗了,晾了起来。丹麦的官员听了儿子的描述,感动了好久。
他把这些东西当作好事传播出去,却时不时收到质疑甚至骂声。有人在网上说他“软骨病”“投降派”,把一些老同事们气得不行,“吴建民在布鲁塞尔为国家挨骂,在日内瓦拍着桌子和人辩论,他们压根儿都不知道!”
施燕华和秘书委屈,把铺天盖地的评论摘给他看。吴建民看到辱骂自己的,最多无奈地笑笑,还会说,“果然要有人出面当这个‘恶人’,不然更没人敢出来说话了。”
可看到“必有一战”之类的话,或者头头是道分析“局势恶化,必须更强硬”的言论,他的眉头就紧锁起来,在家里来来回回踱步,和施燕华一遍遍嘟囔“这不行”。
他心事重重地问年轻的秘书,“到底是谁想打仗呢?不是你们年轻人吧!”心悸之余,他又加倍地疾呼,要警惕民粹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不能让它们“把国家带到沟里去”,破坏发展的机会。
这些人说自己的观点才是“人民的呼声”,吴建民毫不客气地迎上去,“披着‘民意’的外衣,还是一样的套路!”
他想起自己还是驻法大使时,美国要发动伊拉克战争,法国坚决反对。愤怒的美国人把薯条的拼写从“French Fry”改成“Freedom Fry”,把成箱的法国葡萄酒倒进河里,三分之二的美国人都觉得战争“正义且必要”。可10年之后,批判战争的声音成了主流,媒体愤怒地控诉,当年有些人“犯了诈骗罪,犯了战争罪”。
“‘民意’会变化,也无法追究它历史的责任。”吴建民和助手笑着说,自己被骂从不生气,因为“时间会证明我是对的”。他算了算,从自己2008年退休,一些人已经预测了太多次“战争与冲突”,可每次都被现实推翻。
他的热情依旧足,甚至“年轻得不像70岁的人”。和施燕华一起出门,他看见广告牌上生僻的英文单词,就赶紧请教。退休后带着外交部的年轻人出去交流,他总让孩子们带着笔记本电脑,方便他在飞回来的路上就能给部里写一篇“见闻汇报”。
有人问退休后的吴建民最喜欢给哪些人讲课,回答没有犹豫,“学生。”
学校请吴建民去讲课,他几乎从不拒绝,中学有时都来邀请他。施燕华心疼他累,说“孩子太小,就别去了”。可吴建民从来不听,不仅要去,还要查资料,提前很久作准备。
吴建民身边的人说,老人为孩子“破了太多戒”。他从不因为参加的活动影响情绪,即使和别人激烈的辩论,散了场,上了车,云淡风轻。可在一所中学,吴大使问孩子们对日本的看法,有孩子告诉他,去旅游了两个周,觉得他们很文明,值得学习。这样的发言让他特别高兴,感慨孩子们聪明理智,一整天脸上都挂着笑。
他的日程像疾行的车轮转个不停。在法国,刘志明报告问题超过5分钟,吴建民就开始看表。参加宴会不超过90分钟,到点准时离开,劝酒、闲聊一概拒绝。可老白才上初中的儿子为了家庭作业,想要采访吴建民,老爷子拿出一下午时间和他谈心。过几天又有几个孩子想来看他,吴建民高兴地答应。孩子们给他折了千纸鹤,他摸着他们的头说,“可别耽误你们的学习时间。”
他说“年轻人是未来,不能不重视”,脑子里指向的,其实还是世界。他的脸有点像天下大事的晴雨表,身边的人能从那里读到局势的走向。和军队首长谈得投缘,吴建民说“他们理性,国家就安全”,眼角流露出笑意。遥远的国家爆发了战乱,发生惨绝人寰的屠杀,他的脸色变得难看,悲伤在皱纹里流淌。
认识的人夸他还能“再干20年”,吴建民每天游泳、锻炼,走路快得年轻人都跟不上,跨越八九个时区不用倒时差,下飞机就接受采访。
只有身边最亲近的人才知道他或许累了。每天从家到办公室,15分钟车程,吴建民就会睡着,在后排透出微微的鼾声。原本停了车,吴建民就能自己醒来。可开着开着,到了目的地,人们也需要再单独叫醒他了。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晚上,吴建民飞赴武汉的航班连续延误。他抽空回了趟家,自己下了一碗面,吃了半盘剩的菠菜,陪施燕华散了散步。然后赶回机场,凌晨3点半才到武汉。
如果没有意外,他原本要在清晨7点为企业家讲解“如何走出国门”。车祸发生时,吴建民在后排,早和往常一样安详地睡着。只是,再也没有人能唤醒他了。
送别吴建民那天,哀乐被替换成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这是吴建民生前钟爱的乐曲,当他脑中流动着对这个世界的思考时,总喜欢播放它。他曾经说,这部交响乐一片悲壮中,依旧透露出对未来的期盼。(程盟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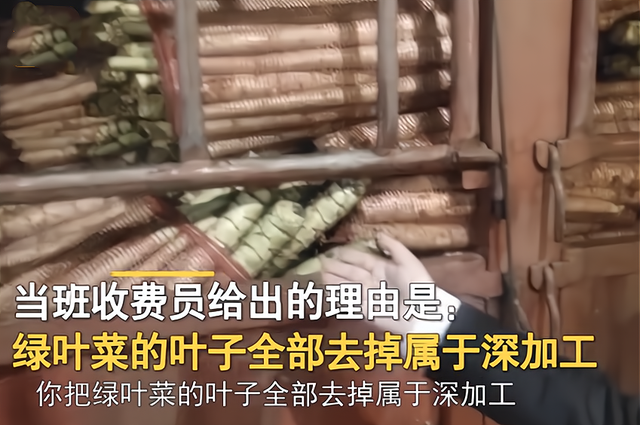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40741号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40741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