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离开一年后,外交家吴建民再次“走”到了人群的最中间。
在法国,人们也从里昂、尼斯、布鲁塞尔甚至大洋彼岸的旧金山赶来纪念这位曾经的驻法大使,其中不乏素未谋面的年轻人。
一年前的这天,吴建民在武汉因车祸去世。一年之后,一位法国“吴建民奖学金”获得者回忆,他们对中国多了理解,知道这是个和平、高速发展的国家。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沙祖康则感慨吴建民“国内外都交了很多朋友,一生都作中外沟通的桥梁。”主持人白岩松说,通过追忆活动,不仅要把吴建民的话讲给和他同龄的六七十岁的人听,“还要讲给40岁、30岁、20岁的人听。”
去世之前,吴建民也在一直努力把自己的话,讲给更多人听。为此,70多岁的他马不停蹄地跑。他一年中多半日子都在外地交流、讲座。今天在纽约、新加坡,隔两日就会出现在南通、盐城。他是各国政要的座上宾,却也会出现在图书馆的公益讲坛上,给老百姓讲“新时代的大国公民”,抓住一切机会讲“不要战争”。
这样的活动甚至连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都没有。主讲人来了就讲,听众们穿着裤衩拖鞋,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有一次,两个大汉因为看法不合吵起来了,吴建民还要当和事佬,“你们一个一个慢慢说,意见我都听。”
在南京,和他差不多岁数的老人站起来质问,为什么要理解日本,忘记国仇家恨,是不是太软弱。吴建民不生气,说要把军国主义和一个国家分开看,他们做错过事,却也在改革开放时提供贷款、技术,是能帮助中国发展的国家,语调依旧不急不慢的。
吴建民生前说,自己在公共场合从未发过火。他不喜欢高声,更不说粗话,作为外交官,连“一贯立场”“坚决反对”这类外交辞令都很少用。他办公室墙上挂着的书法是“润物细无声”。他告诉学生们,说“硬话”不难,可只是发泄情绪,劝服不了别人,那就没用了。
有媒体评论,吴建民的话“你可以不同意,但不会不高兴”。还有的人说,他特别擅长取得共识,总能“把对手变成朋友”。
退休后,他在国际论坛上驳斥美国人关于贸易逆差的发言,挥舞着美国的报纸,“你们自己报道,芭比娃娃20美元,中国人只拿35美分。议员这样还不高兴,我不知道他们怎样才能高兴!”全场听众,包括美国人都憋不住笑。
世纪之交担任法国大使,常有人问他“中国为什么不学习西方民主”。吴建民总是笑笑,不紧不慢地说“我们学习过”。他告诉法国人,一战时中国人跟着英法出生入死,战后却又被出卖,所以后来不学了。很多法国人惭愧地说从不知道这段历史,让吴建民一定要接受他们的道歉。
法国“吴建民之友”发起人,老同事徐波将吴建民比做国家力量的“左手”,这只手灵活,和另一只强力的手截然不同,“如果两只手混了,就要乱套”。吴建民把这码事总结成“交流学”,“你的实力是1,交流本领是0.3,给人的印象分就是0.3。”
为了让“印象分”高一点,吴建民总是忙个不停。他说谈话有事实和细节才能动人,在法国,带着手底下的年轻人早晨8点就起来读报纸,还去法国农民家调研,拜访法国最贫困的山区,非典期间和巴黎市长一起去华人区的中餐馆吃饭。
他身上总带着小本子,听到了好故事、好点子就赶紧记下来。哪怕回国,亲友一起吃饭,侄子侄女说起了新东西,他还是要丢下筷子,赶紧掏纸笔。
在法国,他的时间表按分钟规划,第一场会见往往从早餐开始,两场活动的半小时间隙也要多见一个人。退休后,他跟妻子施燕华提前说好回家吃饭的时间,到点准时进门,吃完饭就又出去开会、办公。
老白是吴建民退休以后的司机,报到的第一天,吴建民就提醒他,“我退休了,但很忙。”可老白还是想不到,跟着一个70多岁的退休老干部,居然3个月都休息不上1天。
吴建民观察过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这些曾经富饶的国家被鲜血和烈火笼罩,挑起战争的大国也身陷泥淖。“开始容易结束难”的战争如同跗骨之蛆,盘踞在所有被波及的人身上。
“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谁举起战争的旗帜谁倒大霉,中国绝不能重蹈美国的覆辙。”
在南极,吴建民听科研人员说,9个国家曾争夺这片土地的主权,几乎兵戎相见。逐利的各国把轰鸣的捕鲸船一艘艘派过来,杀死的鲸鱼来不及立刻回收,就充上气、插上国旗。4000多具鲸鱼的尸体飘在海面上,血红一片,整片大陆都被恶臭笼罩。
直到1959年出了《南极条约》,承认南极洲永远专用于和平目的和不成为国际纠纷的场所或对象,符合全人类的利益。
吴建民踏上南极时,“蓝天白云,湛蓝海水,和雪白的山峦构成绝美的图画。”他说,“南极的启示是21世纪急需的,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一定会迎来共同繁荣的世界。”
“在驻在国的大政方针,是由国家定好框架的。吴建民最难得的是在这个框架里100%地发挥。”曾在吴建民驻法期间担任使馆二把手的刘志明说。国家提出“和平与发展”,吴建民就“努力为国家交朋友”。他坚信对话解决问题更加重要。有的人不信,他不留情面,“还有战争与革命的惯性思维,总想着打一仗,完全搞错了时代”。
吴建民从对抗的时代走过来,作为中国常驻联合国首批工作人员,1971年登上飞往纽约的飞机时,机场挂着的巨大送别横幅是“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在纽约,友好人士邀请中国人去看现代艺术画展,吴建民和同为外交家的施燕华小声嘀咕,“真是腐朽的资本主义艺术,都看不出画的什么。”
可是40多年后,老两口经常一起感慨,要是当初没走出国门,祖国没走向世界,今天的生活不知是什么样子。
1990年前后,吴建民在布鲁塞尔的驻欧共体使团做负责人,东欧巨变让国际关系“一夜间天翻地覆”。
吴建民每次去欧洲议会,总是往座位上一坐,微笑着问,“先生们,咱们今天是讲英语,还是讲法语?”欧洲的高官曾不屑地说,“不知道3个月后,你们这个国家还在不在。”他笑着回敬,“等着看吧,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
他回国当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美国国务卿访华,中方做了细致的安保工作。一位美国记者提问,“你们这么紧张干什么?是不是怕政权不稳,政府倒台啊?”吴建民一字一句地说,“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国家的政府会在经济以两位数增长时倒台!”
散会后,外国记者在走廊里拦住吴建民,表示感谢。“我等你这话等两年了!你这话一讲,美国就明白,中国不会有事了!”
几年之后的日内瓦,再遇到龙永图带领的入世谈判代表团,吴建民提了“至关重要”的建议,“要去见媒体,主动出击,让世界知道中国的声音和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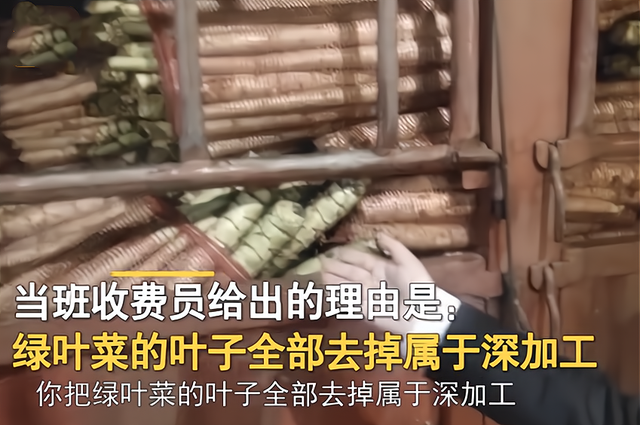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40741号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40741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