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新疆民丰尼雅遗址古墓群的精绝王双人合葬墓,齐头并卧的男女两人均已成干尸,身上覆盖着“王侯合昏千秋万岁宜子孙”的单层锦被,男女主人被30多件丝织衣物层层包裹,不同花色的锦就有10多件。以前听当时的新疆考古所所长王炳华老师讲过,这些丝织物的提取最费时费力,如今再听主持提取的王亚蓉老师讲一讲,就更加明白其中的不易。

1995年王亚蓉老师在新疆尼雅遗址东汉合葬墓的清理现场。(资料图片)
“木棺的空间有限,所有的丝织物都堆在一起,那件著名的锦被上全是细沙,还有密密麻麻的褐色的蛆壳。两具干尸上的衣物更是都堆砌在一处,两边挨着棺架的衣物更脆弱更容易灰化一些,而两人的底部衣物则和棺的底部厚厚地板结在一起,所以需要先将两人分开,单独处理,其次要先把裹在上面的衣服慢慢地打开,褪到两边,然后重新填充海绵,重新固定木棺两边的框架,重新把棺盖盖上,把棺底迅速翻转上来,再处理干尸底部的衣物。这个翻转的过程不能出任何的问题,因为衣物已经非常脆弱了。为此大家试验了很多次,觉得万无一失了,才齐心合力完成。新疆虽然干燥,出土丝织物毕竟脱离了之前的那个环境,既要防干燥,又要适当回潮保湿……”今天我们在欣赏那些尼雅遗址出土的东汉织锦上美丽的花草纹、繁复的翼马对羊图案时,可曾想到过当年王亚蓉老师他们的如履薄冰?
2007年江西靖安东周墓葬现场的丝织物提取堪称近年来最艰难、也最为考验她和她的弟子们的一次。
这个墓的特点是一个墓坑有47具棺木,棺木排列得很密,主棺之外的其他木棺里除了纺织工具外并无其它随葬品,经人类学家对其出土的人骨进行鉴别,均为女性,且年龄从15到25岁不等。打开主棺后,墓主的整个尸身都浸在积水里面,纺织物已经和尸骨、泥沙完全搅混在一起,成为湿软的泥状。为了能顺利提取丝织物,王亚蓉和工作人员将墓旁边的粮库改造成了一个临时的实验室。当时的尸身用竹席包裹着,王亚蓉老师带领大家用泡沫做了一个30公分直径的滚筒,将竹席一点点卷曲,再抱出来放在地上。丝织品和竹席必须要不停保湿,以免脱离原有环境后干裂。

江西靖安东周墓葬现场。资料图片。
“当时我们在水池里放了海绵,用海绵隔着让水漫渗进入,然后大家用手拍动水面慢慢激荡泥沙,那么多双手就在2℃的水中不停拍打,换了几十次水,织物的颜色和经纬才慢慢呈现。”
最后的结果是令人狂喜的。在清理六号棺时王亚蓉发现了黑红似漆器般的精美几何纹锦,这是该批出土文物中最完美的一件,经线密度竟然达到了每厘米240根,也就是说在我们肉眼看来已经非常细的丝其实又是由更多的丝编织而成,一毫米会有24根。足见当时纺织品织造的水平之高。

江西靖安墓葬出土时的几何纹织物。
更多从墓葬出土的东周丝织品最后以一坨“泥”的状态,在纺织考古实验室的冰箱里又收藏了9年之久。直到准备研究之前,王亚蓉才把它取出来,一点一点用羊毫扫落沉积其中的淤泥,用镊子摘除其中的沙粒,光是打开泥封就用了一个多月……
王亚蓉坦言,王 丰富的考古现场经验和精益求精的修复追求一直深深地影响着自己。王 去世后,在许多的考古现场就需要自己一个人立刻拿主意,这对自己是不小的责任。“每一件文物最重要的信息都在现场,包括它的出土位置、颜色、服饰结构、穿着方式等等,这些都是后期研究中最关键的一手资料。特别是颜色,棺内环境在几千年中是稳定不变的、封闭的,可以很好的保存织物原有的颜色。然而,棺盖在打开的短短几分钟后,由于和外界环境、空气的接触,织物曾经绚丽的颜色会因氧化逐渐退掉,这是最令人伤感的事情。”
如果我们将王亚蓉主持或参与过的重大考古排排座,几乎就能串起一部中国纺织考古史,从湖北江陵马山楚墓到陕西扶风法门寺唐代地宫,从北京老山汉墓到辽宁省叶茂台的辽墓、从新疆民丰的尼雅遗址到山东齐故城出土的战国丝织品残片……中国人衣食住行的“衣”的历史,依靠这些考古所得逐渐真实起来。
她复织的丝织品可以成为一座服饰博物馆
无论是从与王亚蓉认识的时间算起,还是从他的复织水平来看,王继胜都是23名弟子中名符其实的大师兄。
作为南京云锦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他和王亚蓉老师的合作是从1986年复制马王堆的薄如羽翼的素纱褝衣开始的,“素纱褝衣复织的难点在于原材料,古人用的丝絮比较细,细到只有头发丝的三分之一。我们现在用的丝都是五眠蚕,蚕蜕一次皮为一眠,2000年前的古代蚕还没进化到五眠蚕的程度,只有三眠蚕。五眠蚕丝的韧度强度不如以前,复原就很困难,因此我们专门成立了养蚕研究所,饲养出三眠蚕,试着解决原材料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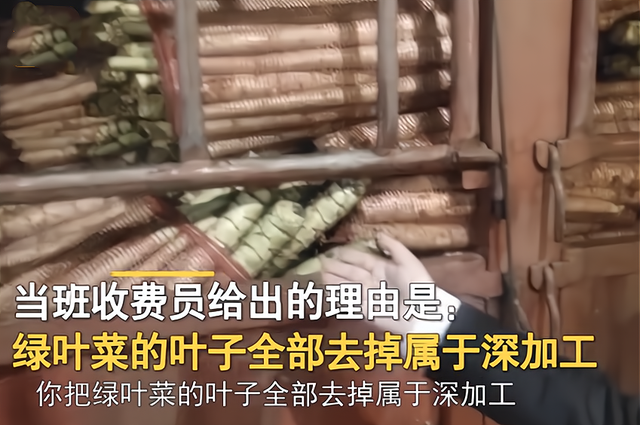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40741号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40741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