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纪录片中的茶园。

▲彩虹下的塔黄。

▲生活中的李成才导演。
受访者供图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张博令
“她”使中国免遭饥饿,让我们繁衍生息;“她”逆境求生,“咬定青山不放松”;“她”治病救人,济世仁慈遍九州……
“她”也影响着隔洋相望的日本饮食习惯;“她”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新西兰的出口结构;“她”还“征服”了四百年前如日中天的大英帝国,最终影响着全球60多个国家、30亿人口……
“她”是孕育了华夏民族的中国植物,也是李成才导演的纪录片《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中的一个个主角。这部BBC级别的纪录片,让我们能隔屏嗅到乡土淡香,讲述着你我身边熟悉又陌生的“中国植物”故事,是国内第一部植物类纪录片。
“大气内涵的题材;海量丰富的知识;上天入地的拍摄;新颖脱俗的风格,文艺抒情的词藻;内敛平实的剪辑;悠扬诗意的音乐。”这是网友对此作品的评价。
草木缘情
李成才早年的纪录片多是将世界的故事讲给中国听,如《大国崛起》《华尔街》和《货币》,展示金融、历史等领域的世界故事。这次他选择根植中国,“把我们自己可能都不太清楚的故事给讲清楚”。
或许我们用味蕾品味过“她们”的果实,用锄头改善过“她们”的生活,用镰刀收割过“她们”的生命。但我们中的大多数,对“她们”都一知半解。
“早年间,有两本书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刺激,一部是英国人写的《稻米全书》,一部是美国人写的《茶叶全书》,这些耗费几十年心血,书写中国植物的作品,都不是中国人写的。”李成才导演说,他想为中华文明做点什么。只拥有四千多种植物的英国,是拍摄大自然最成功的国家。而拥有三万多种植物的中国,却缺少一部讲述中国植物的影片。
这部十集的影片并不算长,但200多人的创作团队,100多位摄影师,200多位植物专家参与创作,走访英国、新西兰、日本、印度等7个国家,国内27个省,拍摄了近1200小时的素材,耗时近3年,运用4K摄影、无人机航拍、延时摄影、定格动画、显微拍摄、动画特效,这才为大家呈现出高速弹射中的桑树雄花,与甲虫斗智斗勇的海芋,水中发芽的千年古莲子……
植物题材的纪录片在业界是十足的冷门。有专家用一幅既有人,也有动物、植物的画做过实验,测试人们对三者的关注情况,结果统计,近七成人将目光首先停留在人上,其次是动物,只有不到一成的人会首先关注植物。但纪录片投资成本正好相反,拍摄植物成本最高,然后是动物,成本最低是拍摄人物。
李成才导演出生在河北唐山的一个乡村,童年常与各种农作物相伴,也许是那时埋下了热爱植物的种子。工作之后,他因为一次演讲来到武汉大学,碰上一个讲述植物与人类关系的展览,催生了他拍摄植物类纪录片的想法。
通过《草木缘情》,他了解了一些植物大数据,他清晰地记得“第一本诗歌总集《诗经》中一共出现了136种植物”,人们总爱借物抒情。他时常告诉自己,“这些伟大的中国植物应该被镜头记录,应该得到尊重。我们也应该好好感谢大自然的独特馈赠,当高楼大厦都建起来之后,我们应该为人类文明做点什么”。2019年北京召开的世界园艺博览会,正好为他提供了一个纪录植物的契机。
“就算我不做,将来也一定会有人去做,我相信植物的这种力量和魅力,一旦开始反思我们的源头,追着追着,也会追到植物上。”李成才对“中国植物”信心满满。
翻山越岭,只为最美的你
“玉骨冰肌绝俗缘,悬崖峭壁傲霜天”“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芝兰生于深谷,不以无人而不芳”……危境中的植物作为情感的载体,是诗词的常见题材。但现实中,这些植物往往“藏身”于无人区,很难确定其具体坐标。纪录片需要实景,不能像诗词一般不受限制,一笔带过,摄制组最基础的工作便是找到这些植物。
毫不夸张地说,找寻“深谷”“峭壁”等绝境中的植物,是摄影团队的“日常”。许多植物的找寻甚至只能凭借耐心与运气,让李成才印象最深的植物是塔黄——拍摄过程中最难找到。
塔黄虽颜色鲜艳,且在花期内能长到2米高,但其生长环境异常严苛,一般在青藏高原海拔4000米以上、雪线之下。在偏远地区的流石滩上,碎石中求生的塔黄没有主根,还可能随着流石的运动发生位移。
找寻塔黄之路异常艰难,“别看塔黄是藏药,很多藏民并不熟悉,得自己去摸索”,摄制组只能靠着昆明植物所专家宋波贴心画下的“寻宝图”慢慢探索。目标在某个不知名山沟边的一片流石滩中,但谁也不知道流石滩此前是否发生过位移,是否有人提前发现、抢先采摘。这也就意味着,翻山越岭后摄制组仍可能无功而返。
“再加上没有路、没有人、没有电、没有信号”,摄制组带着帐篷兵分三路找了三天,遇上过大雨和塌方,第四天终于在一个山坡后“偶遇”塔黄。
一段时间的驻地观察后,摄制组发现塔黄所在的区域几乎每天都在下雨,工作不得不冒雨进行。就在准备上山拍摄时,负责运输设备的马受惊失控,马脖上的绳子还套上了录音师的脚,致使录音师被失控的马匹拖行数米,所幸受的只是轻伤,拍摄还能继续。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摄制组拍到了阳光中、冰雹下,乃至与彩虹相伴的绝美塔黄。
奔赴非洲的摄制组也有过一段看不见的惊险体验,为拍摄黄花蒿素材,摄制组根据疟疾新闻,去往位于非洲的马达加斯加,在试图进入目标区域时,被告知该地区已成为疫区,不能进入。
为能进入疫区,摄制组通过马达加斯加卫生部向当地医院捐赠了价值250多万马币的青蒿素类药品(当时1元人民币能兑500马币),进入疫区后还发现当地正在爆发鼠疫,仅摄制组所在的医院就有六个鼠疫病人,“连一直不戴口罩的当地向导都默默地从口袋掏出口罩”。
在落后医疗条件中,每多待一天他们就多一分风险,染上足以致人死亡的疟疾和鼠疫。摄制组就是在这种无形的威胁下战战兢兢地记录下黄花蒿影响下的非洲疫区。
为了拍摄珙桐开花,他们搭起了一个6米高的“简易”摄影棚,拍摄了两个多月;为了拍到野生大熊猫,他们在秦岭深处拄着拐杖探了四天;为了拍摄即将弹粉的桑树,“追着”雄花各地跑……
让植物开口“说话”
植物纪录片的特殊性对摄影提出了挑战,人物纪录片可以安排场地,可以与拍摄对象沟通协调,但植物“听”不懂人类在说些什么,只会按照自己的生长规律慢慢成长。
表面静默的植物同人类一般,有生老病死,有与其他物种的合作与博弈,温情与厮杀……纪录片中的大自然仿佛激流暗涌的江湖一般,让人不难体会到为何古人会将植物作为感情寄托。
让生长极其缓慢的植物“动”起来,不仅需要摄制组数年如一日的坚守与等待,还要有与植物相配套的特殊拍摄方式,要用巧妙的镜头语言表达植物的情感,要用受众能广泛接受的形式讲好植物故事,让植物开口“说话”。
音乐是人类的第二语言,配合动人的旁白,更能让观众感受到植物的生命与成长的魅力。为此,摄制组邀请作曲家代博依据剧情作曲,请国际首席爱乐乐团演奏,“有三十多段,七十多分钟的原创音乐”,李成才告诉记者。
植物生长画面对影片质量也尤为关键,为获得植物生长的特殊镜头,摄制组还在办公区搭设了一个近200平米的摄影棚,有一批专门负责棚拍的摄影师。他们不用去户外满世界找植物,但一点不比户外摄影轻松。由于国内没有专业的植物摄影师,摄影师需要学习植物的生长习性以及每种植物的不同特点,“我们的摄影师要跟植物学家和导演商量,该用什么样的土壤,用什么样的水,用什么样的肥料,用什么样的光才能拍得最好。”这需要摄影师们成为植物领域的专家。
一组几秒钟的千年古莲子镜头,棚拍导演足足拍了三个月。古莲子极其稀有,整个中科院系统只给了摄制组三颗,其中一颗需要从中间切开,拍摄微观下的横切面,“他们切莲子的时候,怕切坏了,手都在不停地抖。”李成才导演回忆,“他们没有试错机会。”
棚拍摄影师李佶托在拍摄中成为了一名“斜杠青年”,他不仅要做摄影师,还得是“保育员”。莲子的发芽生长一般需要三十天,拍摄期间,不仅要确保水中莲子的位置固定不变,还要确保莲子成活的同时水体不会变得浑浊。“任何一点细小的事物,都有可能导致拍摄前功尽弃”。为了控制水体,李佶托用紫外线灯烘烤水体,中途还因直视紫外线造成短暂的失明。是他们的敬业、专业让植物们“开口”说话。
中国植物是华夏大地的遗产,为了保护这些濒危物种,对其在影片中的呈现,摄制组隐去了准确坐标。曾有一些旅行社找到摄制组,想开辟影片中的植物栖息地作为旅游线路,都被一一拒绝。
熟知,殊不知
“人类诞生前,植物便立于天地之间。”青藏高原的隆起形成了世界第三极,造就了独特的地理环境与生物类群,从衣食住行到药用审美,中国植物孕育并陪伴了华夏文明的诞生。
中国植物为我们所熟知,人人都能讲出几种耳熟能详的品种。中国植物同时为我们所不知,比如新西兰国果猕猴桃起源于中国;水稻改变了日本人的饮食结构;桑树间接推动了文艺复兴;茶叶“征服”了全球30亿人……中国植物正在影响世界。
“新鲜的稻米托起鱼虾,平分秋色、相互映衬。”这便是我们所熟悉的邻国佳肴——寿司,日本人民最喜爱的食物之一,稻作文明与海洋文明在小小的寿司上完美融合。其中托起鱼虾的新鲜稻米便是由中国传至日本,中国植物改变了邻居的饮食结构。
大约3000年前,随着人口的流动转移,水稻通过朝鲜半岛传入日本北九州的北端,而后逐渐普及。水稻传入日本之前,日本人民的食物多来源于打鱼和狩猎,如今,水稻已成为日本不可或缺的粮食作物,甚至还催生出以水稻作为画布创作巨大图像的稻田艺术。
中国植物不仅在食物上影响着世界,也是推动世界艺术创新的重要力量。起源于中国的白桑在公元12世纪被传播到欧洲,随着白桑传播的还有中国的织造技术。阳光充足、气候四季分明的意大利就是受益国之一,佛罗伦萨的名门望族,得益于白桑的传播,基本垄断了丝绸产业链。其中美第奇家族赚得盆满钵满,一代代美第奇家族成员通过丝绸产业获得的财富,对文学家和艺术家们提供了大量赞助,也间接推动了影响世界的文艺复兴。
略带讽刺的是,被我们称作“百果之王”的猕猴桃原产于中国秦岭以南和横断山脉以东的大陆地区,但却在引入新西兰后“声名鹊起”。100多年前,英国“植物猎人”威尔逊在湖北宜昌的山区找到了一个被当地人称作“羊桃”的藤本植物,并将其种子寄往英国和美国,恰巧这些种子全是雄株,无法结出果实,猕猴桃的首次远征就这样以失败告终。
后来猕猴桃又与新西兰女教师伊莎贝尔相遇,被她带回家乡。新西兰冬季无连续低温,春季无霜降,土壤疏松透气,恰好符合猕猴桃的生存需求。更幸运的是在新西兰撒下的种子培育出了一株雄株,两株雌株,6年后猕猴桃在新西兰开花结果,获得新生。经过新西兰人不断驯化与改良,猕猴桃得到广泛种植,还有了一个以新西兰国鸟命名的名字——kiwifruit。如今,新西兰猕猴桃远销59个国家和地区,成了国果。中国作为猕猴桃的故乡,则变成新西兰猕猴桃最大的销售市场。
在《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拍摄期间,有外媒曾问李成才导演是否又要开始讲“你们国家如何厉害的故事”。李成才回应:“我们只是在讲两件事,第一讲自然对我们的馈赠,从中国开始的植物故事。第二才是人类的创造力,讲祖先如何将这些植物变为我们华夏文明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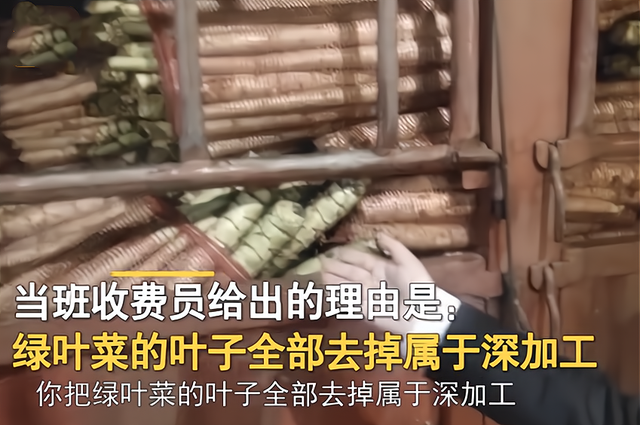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40741号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40741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