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陉几十年也出不了这样的名人”
2014年3月12日,植树节,关于“种树老人”的第一篇报道发出。两天后,贾海霞接到村支书电话,《石家庄日报》要来采访。“那是最激动的一次,党报啊,来采访我们,多不简单!”
贾海霞家写字台正中间摆的是和石家庄市委书记孙瑞彬的合影。两年前,孙瑞彬曾出现在他家小院,告诉他和贾文其“一棵树就是一个除尘器,一片林就是一个制氧站”。
贾海霞没听过这么“有水平”的话,他把这句话当作座右铭,“别的媒体来了,我们也学着说。”带着身残志坚、绿化环境的标签,两个人被评为“2014感动河北年度人物”。
经过河北当地媒体连续发酵,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贾文其和贾海霞接到很多采访邀约。贾海霞拉着曾经走南闯北的贾文其的袖子,第一次去北京、合肥,第一次坐高铁、飞机,感觉“光荣、骄傲”。
今年三月份,贾海霞把一直在外打零工的老伴叫回家帮忙联系树商,“儿子二十了,树也长大了,我们想把树卖了,我给儿子结婚,贾文其拿着钱养老。”
“买树的人来看了三次,我们的树有大有小,人家说平均下来按一棵一百算。”贾海霞老伴说。
树还没来得及卖,CNN的一条两分半钟短片再次把他们推上舆论浪尖,五六月份,中外记者突然涌进来,事情开始“变味了”。
村支书刘彦明、县宣传部新闻科负责人高靖华那段时间每天在贾海霞和贾文其家“上班”,负责接待和引导记者。高靖华说,“井陉几十年也出不了这样的名人。”上次井陉县引起媒体广泛关注还是2007年的红心鸭蛋事件。
来访者的套路都差不多,先让贾海霞爬树砍树枝、贾文其背着贾海霞蹚水,再问他们为什么种树、怎么种树。最夸张的时候,树林上空三个无人机同时在转。
有一次,贾海霞正在“表演”爬树,下边的两拨人打起来了,一拨人走动影响了另一拨人的拍摄。两边越打越凶,贾文其没法拉架,贾海霞赶忙从三米多高的树上下来,摸索着把他们拉开,劝说和气以后,再次爬到树上供他们拍摄。
贾海霞很无奈,五十多的人了,最多的时候他都记不得自己一天要爬多少次树。“我们还不如耍猴的,猴子上树还有人扔硬币呢,我们都没有。”
六月份,有一家电视台拍摄贾文其背着贾海霞过河的画面,来来回回走了十次都不满意。天气很热,两个人感觉头重脚轻,全身没劲,强撑着精力完成当天的拍摄,第二天就说不出话了,发高烧,在卫生所打了一周多点滴。
贾文其实在没有面对镜头表达的欲望,他喜欢安静的生活,看看书、下下棋、写写字。“让人不舒服的事儿实在太多了。”贾文其说,“但是人家大老远来了,我实在不知道怎么拒绝,有什么要求我就想尽量满足。”当时,四个杭州来的学生想采访他们,他们一时抽不出时间,贾文其安顿学生在自己屋里住下,自己找别的地方凑合。
成名使他们俩成为村里“不自然”的人。贾文其带记者在村里或河滩上走,村民都会盯着看,有人阴阳怪气地说“又视察工作啊?”还有村民背地里讲,河滩上的树不是他们种的,是自己长出来的。
贾文其对名气和关注度越来越麻木,他经常想“什么时候才能熬出来啊。”
“名誉太不现实了”
这一轮的舆论包围促使贾海霞和贾文其改变了卖树的计划。“我们一开始种树就是想等长大了卖钱,后来得到的关注和认可多了,好像钻进套里了,都说我们是榜样,树也不敢卖了。”贾海霞说。
贾文其的解释更简单,“我们一边砍树,一边接受采访,不合适。”
他们都清楚河滩上种树有风险,村里老辈人都说冶河每过十到二十年就会发一次洪水,上次大水正好是二十年前。五月份贾海霞还说,“这河边就是水,要是涨一次,发大水了,马上就冲完了。”
县长在他们村边接受《焦点访谈》采访时表示,“一旦发生了一些不可预见的灾害,比如树木受到损失了,我们林业部门也可以给他一定的经济补偿。”
当期《焦点访谈》还未播出,洪水就来了。摄制组再次来到村里拍了残枝漂在洪水中的画面。新华社报道,截至7月26日,井陉县共有20.8万人受灾,死亡38人、失踪33人。
县宣传部新闻科负责人高靖华说:这次井陉县受灾严重,有的镇子道路被冲毁至今还在施工,没有钱也没有名义通过财政拨款给他们俩的树林补偿,以后他们再种树,可以从别的方面给他们提供帮助。他跟贾海霞讲,“要有全局观,不能因为是名人就特殊对待。”
洪水过后第二天早上,上游村民沿着河道打听有没有人看到尸体。贾海霞想,人家命都没了,这些树没了就没了吧。
五月份面对舆论称赞,贾文其曾说“塞翁失马”。一语成谶。“现在树没了,这就是狼吃了小孩——活该。”
舆论关注曾给两人带来现实的帮助,他们拿到过多笔来自政府、残联等单位的奖励或救助。五六月份好几位爱心人士到家里放下米、面、油或者装着一两千块钱的信封,名字也不留。假肢、空气净化器、橱柜甚至化妆品企业都来送温暖,“拿点东西到这跟我们一起拉个横幅拍张照就走了。”
贾文其早就想到后山上去种树,“不用老担心会被河水冲走”,一直受困于没法浇水。今年春天,网友为他们募捐了六万块钱,在山上修蓄水池。4月份动工,两个人满怀期待,每天都盯着施工。
十几天后,施工结束,没有阀门也没有防护栏,包工头说六万块钱用完了。这时有村民拿出山上土地的承包协议书,向他们宣示主权。贾文其觉得尴尬,不愿再提上山种树这回事。
7月19日的洪水结束了两个多月的喧嚣。这半年,树没了,很少有媒体再来,爱心人士也不见了。两个人过上了清闲平静的生活。
他们等待明年开春,重新开始。贾文其说,“庄稼人不怕这个,土地冲走河滩在,树没的时候我就准备着明年再种了。”
贾海霞也是同样想法,“树我们还要种,这回我们不会再图热闹了,种几年就卖。名誉太不现实了,能吃还是能喝?只有把事情做成了,才能挺起腰杆做人。”
贾利鹏理解父亲的心情,“十几年了,一出家门就能看到河里绿绿的一片,现在啥也没了,看着可不得劲儿。”他说:“树没了没事,人还在,我爸想种就接着种,他岁数大了种不动了,我还可以帮他种。”
12月的冶河湍急清冽,贾文其问我,“你看我们这河像不像《三国演义》里的滚滚长江东逝水?”
他一个人沿着河边往前走,突然唱起“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带我们走近人间天堂。”远处,夕阳隔着雾霾散发出微弱的光,太行山脉披着一层朦胧的昏黄。
采写/新京报记者 杨静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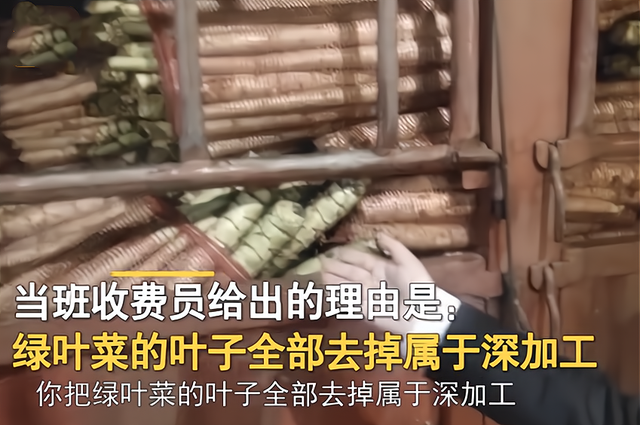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40741号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40741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