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3月13日,是平常的一天。
对于拉卡拉,以及先后六次创业的孙陶然,这一天,并无大事可叙。
这一天,孙陶然需要去干三件事儿:接待一群从西部某城市过来考察的地方官员;接受我们的采访;去联想控股参加一个由柳传志主持的会议。
从表面上看,这一天所发生的事儿都平静如水,构不成企业发展史上的轰轰烈烈以及重大因果节点。但正如德鲁克所言,企业的常态总是单调乏味,没有那么多激动人心的事情。因此,我们不妨从小事开始进入。
——一张长条形的黑色会议桌,孙陶然坐在桌子的正中间,旁边是拉卡拉负责采访记录的工作人员。因为前一晚晚睡的原因,疲倦写在孙陶然的脸上,但仅仅是写在他推门进屋之前的脸上。落座后的孙陶然,理了理深灰色的西服,拿出了老练而职业的专注。他对记者说:“你问我答,什么都可以问。”
但显然,他并不是一个可以无话不谈的受访对象。对于一些在传播上他认为可能会让自己“掉进坑里”的话题,他会本能地反问采访者:“你觉得呢?”“怎么会呢?”
总之,接受采访,肯定非孙陶然所爱好,但这却是一种需要,他负责把需要变成爱好。正如他所说,“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人,不喜欢在公众场合演讲,但是你作为总裁必须去演讲。”
把“需要”变成“爱好”是一种能力。这也是2013年3月13日孙陶然处理这三件工作的职业态度。至于喜欢做的,不喜欢做的——答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类似的这一天,类似的因果关联,处事方式,构成了他创业22年来的一种生活形态——也构成了不同人对人生的不同掌控能力。
22年,孙陶然在六个不同的领域连续六次创业。在外人眼中,他创造了中国公关第一股蓝色光标,成就了恒基伟业商务通,再到今天中国最大的线下电子支付公司拉卡拉,履历光鲜——相当于登到山顶好几次,而且每次路线还不一样。
但在孙自己看来,每一家成功的公司都是九死一生的幸运儿,也都经历过现金链断流、发不出工资、市场推广手足无措等数不清的沟沟坎坎。那些一年创立两年融资三年上市的创业神话,其实是那些成功者包装出来的“毒”。
解毒——是他企图送给那些真正适合创业的人的一份礼物。
不适合创业的人就别创业
如果这个世界明天就要毁灭了,那你还会不会选择去创业?
若你回答是的,那你就属于天生的创业者,至少不属于那些为了就业而去创业的人。
天生的创业者,在人群中的比例不超过百分之十。这很残酷,却是规律。
孙陶然认为自己属于这百分之十。
他争强好胜,从小便如此。父亲是大学建筑系教授,母亲是医生,他成绩好,跟班里那些“坏”孩子的关系更好。直到今天,孙陶然都认为“孩子王”这个特质,是一个创业者所需要的。孩子王获得的号召力,并非行政权力所赋予,那又是如何产生的?有什么值得借鉴的?
1987年,孙陶然以吉林省文科第四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经管系。多年以后,在厉以宁教授的一篇回忆文章中,他提到了北大87级所诞生的一群企业人才,诸如百度李彦宏、蓝色光标赵文权和西藏旅游欧阳旭等。
只是,毕业后的孙陶然与赴美国再读书的李彦宏有着不同的际遇。他被学校分配回了吉林当地一家建筑公司。据说,这样的分配结果,是因为狂傲的孙陶然在校期间开罪了当时的一位校领导。
孙陶然回吉林了。只是去公司报到的第一天,他便顺手办理了停薪留职。
他应该有些不屑。因为彼时的北大校园思想活跃,讲座不断,高手云集,用一句时髦的话描述,他是开了眼界的人。当分配有了发配的味道,孙陶然说,什么户口什么住房什么公职我都不要。
他本意是去联想。对于这家就在学校旁的公司,孙陶然早在大学期间便瞄上了。当时,诸如“有多大本事就给多大舞台”、“个人利益融入企业需求”的联想口号,让孙陶然感到新鲜、振奋。当然,暂时的失之交臂并不重要,因为多年以后,他又通过另一种方式成为了联想大家庭一员。
总之,自从踏进北京城的那一刻起,孙陶然便决心留在这座城市。他父亲那一代从农村去到了省城,他认为自己这一代理应在京城扎根。事实上,孙陶然这一代登上历史舞台的背景,正是商人作为一个阶层,在中国慢慢有了自己的地位。中国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革命。
在动荡变革年代,谁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领导者?美国精神病学专家纳赛尔 伽米说,表现出色的领军人物通常都有精神方面的疾病。比如,在华为最艰难的时期,任正非就患过抑郁症和焦虑症。#p#副标题#e#
孙陶然尊重任正非、柳传志这两位中国最优秀企业家。但他不认为自己有过焦虑,无论是第一次创业还是第六次创业。
他雄性激素旺盛,精力充沛,熬过创业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九死一生。但他也认为压力再大,领军人物绝不能垮,面对员工面对外界,也要“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
当然,这些人也需要透气和呐喊。孙陶然酷爱户外极限运动,登顶后喊一嗓子,就像苍原上的狼。
第一次呐喊
曾有媒体问孙陶然,你跌的最大的跟头是哪一次?
孙说,我没跌过跟头。什么人会跌跟头?一个瞎子在前面有沟的时候会跌跟头。
对方又问,创业22年,你最失败的一次是什么?
孙说,如果你失败了正常地承认失败,这没有问题,但我没有失败过。
——这真是一个有趣的情景。首先,双方对于失败的界定可能不一样;其次,孙陶然身上确实有一种近乎偏执的自信。
这种自信来自天性,也来自北大系统性教育所带来的价值观影响。直至今天,孙陶然都对这所大学充满感情:他是北大企业家俱乐部的常务理事;六次创业,公司的物理半径几乎都在中关村附近。
更重要的是,他的那帮哥们很多都和这所学校有关。
1991年从吉林回到京城的孙陶然当起了北漂:没有单位、没有住房、没有户口。没有户口就意味着没有粮本,就不能买粮,但孙陶然并不觉得有什么,至于今天流行的“安全感”一词,他压根就没这概念。
他租住在五道口的一间平房里。一天,一位朋友找到他,说自己在一家名叫四达集团的公司上班,是公关部总经理,也是光杆司令,邀请孙陶然一起干。
孙陶然说自己没有北京户口,这个人说,四达集团是一家集体所有制企业,能招临时工。
就这样,孙陶然去四达集团上班了,每月工资两百多元,分管公关宣传。干着干着,孙陶然觉得还有点意思,于是,他又找到了当时正借住在自己小平房里的赵文权。
赵文权是孙陶然在北大的同级校友,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结果进去后,先下基层培训一个月,最后卖了4个月鞋。
听了孙陶然的“叨叨”,赵文权心动了。他第二天便跑百货大楼请求调走。领导说不行,赵说那我不上班了。于是,什么户口、档案,也都不要了。
据说,当时在五道口那间平房借住过的朋友,还有现在拉卡拉的资深副总裁戴启军。
一帮哥们朋友就这么乐呵乐呵地过着。一次,一位分配到政府机关工作的同学分了几斤鸡蛋,大伙就跑到孙陶然的平房里边打牌,边用电热杯煮鸡蛋。牌打了一晚上,鸡蛋蘸着酱油也吃了一晚上。
1994年,孙陶然接任了四达广告公司总经理。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与北京青年报签署合办《电脑时代周刊》的协议。
事实上,这应该算是孙陶然在四达平台上的第一次创业。
《北京青年报 电脑时代周刊》是中国第一批产经周刊,开创了全国大众媒体开办产经周刊由薄变厚的时代。该刊的理念是用大众看得懂的语言,用他们喜欢的方式介绍电脑知识。简言之,一本市场化的刊物。
两年之后,《北京青年报 电脑时代周刊》的广告客户席卷了当时所有IT主流品牌。全年的广告版位在年初的时候便销售一空。而孙陶然出任四达广告公司总经理时,公司账面上只有3万元,1995年公司即盈利100万元,1996年达800多万元,1997年便突破了千万元大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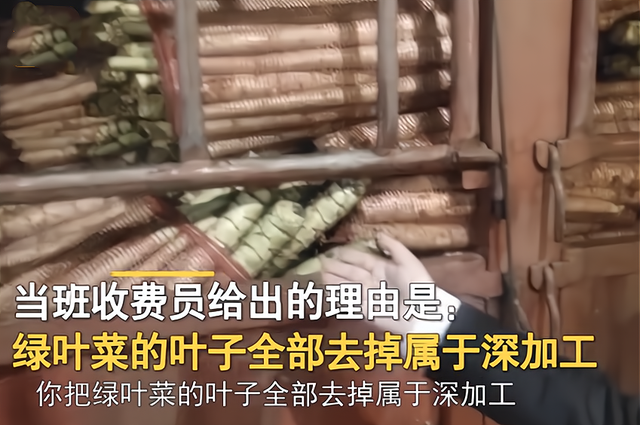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40741号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40741号 


